编者按
为充分体现我校老教授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进一步推进老同志在当前“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背景下发挥作用,2019年,我校设立了老教授课程思政工作坊。在老干部党委的统筹下,由老干部工作处牵头负责,联合退休教职工工作处、教务处、党委教师工作部等部门,共同推进老同志参与学校中心工作。2020年,工作坊联合《复旦》校刊,开设“老教授谈教书育人”专栏,特邀各院系老教授结合多年来教书育人的经验,围绕“我所开设过的课程”、“我当年是怎么编写教材的”、“我当年是怎样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的”、“我们当年是这样备课的”等主题撰写文稿,传授经验为主,讲述当年故事为辅,为广大在职教师备课、教学、教材编写等方面提供借鉴和参考。
百廿复旦正青春,教书育人薪火传。“老教授谈教书育人”专栏系列文稿,既在《复旦》校刊定期发表,也在《校史通讯》和复旦主页“相辉笔会”刊登,并陆续在“旦园枫红”公众号加以推送,通过个人回忆与历史见证,展现120年来的复旦故事、师德传承和教书育人的温度。本期与您分享府寿宽教授的回忆文稿,一同领略于同隐教授当年教书育人风采风范,并借此表示敬意和谢意。
我的导师于同隐先生

府寿宽
(1940- ),江苏吴县人。1957年考入复旦大学化学系,1962年考取为于同隐先生的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83-1985年在Polytechnic Institute of New York 的Vogl教授课题组作进修学者,1993年起任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教授。1993-1994年在美国Coating Research Center EMU作访问科学家。曾任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副系主任、系主任(1995-1999)。2006年7月退休。
01
于先生1917年生于江苏无锡,1934年考入浙江大学化学系,1938年在抗战离乱中毕业。1943年浙江大学任教。1947年赴美留学,1951年获美国密歇根大学有机化学专业博士学位,同年回国任浙江大学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到复旦大学化学系任教授,并从事有机化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58年,41岁的于先生领衔创建复旦大学高分子学科。
我1957年秋考入复旦大学化学系,58年秋开始上于先生的“有机化学”课,60年秋大四时被分入刚组建两年的高分子专业,本科毕业后考取为于先生的研究生,66年春研究生毕业留校。之后一直在复旦的高分子学科工作至2006年7月退休。退休之后,也一直和于先生有较多的往来,直至2017年2月6日在病床旁送别他。
于先生仁者寿,享年百岁。作为和于先生相处时间最长的学生和同事之一,我在此记述和先生相处的五十五年中的点点滴滴,以为对恩师的怀念和纪念。

于同隐(1917.8-2017.2)
02
于先生在学科建设上很有战略眼光。于先生出身于有机化学,但他在规划布局上并没有局限在自己擅长的高分子化学领域,而是带领大家一起学习自己并不擅长的高分子物理。至1965年,高分子教研室便设立了高分子化学、高分子物理、高分子工艺和高分子辐射化学四个组,形成较为完整的学科布局。这在当时的全国高校中是不多见的,为复旦高分子的厚积薄发奠定了基础。
我读研究生的第一年主要是上课,政治课、英语课和各种专业课。于先生的教学方式就是带研究生们一起阅读当时高分子专业的著名论著。安排我们三个年级的研究生们一起读Tobolsky的《聚合物的性能与结构》和Bamford的《高分子自由基化学》等原著,二周一次集体阅读讨论,每次由一位同学上台讲读一章,然后与于先生一起讨论。我的研究方向是高分子化学,于先生特意安排我读Lenz的《有机化学结构理论》,学习方式也是二周一次讨论,不过是于先生和我一对一,他听我讲读并点评指导。
我在大学二年级以前学的是俄语,英语是第二外语,且只在四年级学了一年。读研究生时,于先生要求外语课改为英语,我英语基础差,被分在慢班。所以,跟于先生一起读英文专著的吃力程度可想而知,真是压力山大。但也就是这样被逼着啃下来了。一年的英语专著阅读下来,我的“哑巴英语”也有所长进。记得研究生二年级时,英语慢班的老师吴辛安教授给我作业的评语是“much improved”,备受鼓舞。
我们高分子合成方向研究生的实验室在跃进楼的306,于先生的办公室就在隔壁的308。于先生会不时踱过来靠在实验桌旁和我们聊聊天。这样,时间久了,就形成了一种轻松、平等,无拘无束的师生关系。
研究生一年级时还有一件事至今难以忘怀。
在62年的10月份吧,于先生突然叫我去他办公室,告诉我:“今年上海市化学化工年会要开始了,我给你报名了,报告内容就是“乙酰乙酸乙酯的制备”,你准备一下。”
我一下子有点懵。因为这是我60年暑假期间,在王季陶先生的实验室里跟着做的一点实验工作。就是在制备工艺上有所改进,能有效提高产率。我从来没跟他人说过,于先生怎么会知道?可能是王季陶先生在教研室中说过,于先生的细心和用心可见一斑。
这样,我就被“赶鸭子上架”了。其实是很简单的一点工作,论文摘要仅几行字。但对我来讲,这是生平第一次做会议报告。报告的地点是上海科学会堂二楼大礼堂,主持人是有机化学名家黄耀曾先生,这下子更是让我忐忑得不行,现在也回忆不起当时是怎样把报告讲完的。这件事之所以不能忘怀,是因为后来才逐渐感悟到于先生对我的这种“赶鸭子上架”式的鞭策,培养,提携,直至九十年代我还一直领受着。
03
1963年9月,进入研究生二年级,除了英语学习和选修课外,就要进实验室做课题了。
一天,于先生踱过来跟我说,“阿宽,我给你一个题目,你先做起来,动动手。”什么题目呢?就是大分子偶氮染料。并说“要用到的试剂,我已经给你订购了。用这个药品要注意安全。”
他这么交代过后,下面具体怎么做就是自己的事了。从不催进度,但也不是完全不管,遇到困难时会一起讨论解决,并推荐向相关的专家请教、学习。这个课题除了第一步有点新意和难度,后面就是很普通的有机化学反应了。很明显,这是一个练练手的题目,大分子上的化学反应,并不是我的研究生论文题目,我还是很认真地查资料,做起来了。
这时有个64届的同学张世琳,很聪明的一个人,提前进我们实验室,做他的本科毕业论文,就跟着我一起做。
虽然起步有点难,但总的进展还相当顺利,到64年的初夏,我们就做出了多种颜色的聚苯乙烯偶氮染料,而且还试着去染棉花、羊毛和腈纶纤维。这期间于先生经常会饶有兴趣地踱过来看看,而且建议我们关于怎么做染色试验,要去问问行家。
说来也巧,我本科同学沈中和的父亲沈鼎三先生,是当时上海染料所的所长。我到他家中拜访,沈先生很热情,让我们去他所里看怎么做染色试验。后来还帮我们做了多种大分子染料在棉花和腈纶纤维上的染色牢度测试。

1963年,府寿宽和于同隐先生在西湖游船上
1965年春,我返校回到实验室不久,于先生又从隔壁他的办公室踱来了。这次是给我研究生论文课题来了。他拿出一篇美国Hercules Co.在60年代刚发表的专利。内容是用一个三官能团的苯基三氯硅烷单体,经缩聚生成可以溶解的像梯子一样的双链“梯型聚合物”(Ladder polymer)。这个结果和教科书上所说的用三官能团单体通常得到的是交联、不溶解的网状聚合物的说法是完全不同的。
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激起了我的兴趣。差不多三个月吧,我就做出来了,确实可溶解,能成基本上是无色透明的膜,电阻率高达10的18次方。我们想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名字,称它为“有机云母”。于先生看到这个结果当然很高兴。
那个时候,我们竭尽全力想把这个成果推向应用。为了能大批量地生产成膜,于先生还专程带着我去当时的上海感光胶片厂,参观流延成膜的设备和工艺。说来也巧,这𠆤胶片厂和我家同在一条路上,相隔仅一个半街区。那天参观完后,得知我家就在附近,于先生兴致很高地说“去你家看看”。这样,我大概是于先生的学生中第一个受到于先生“家访”待遇的了。
1966年4月,我通过了研究生论文答辩,5月毕业,继续留在高分子教研室工作,6月1日入职报到。

1965届复旦大学理科研究生毕业照。那时全校理科研究生毕业生仅30余人。前排为校、系领导,其中左六为苏步青副校长
04
1976年,我从“五·七化工厂”回到了离开近6年之久的高分子教研室。不久,年近花甲的于先生担负起重建高分子专业的重担。关于年近花甲的于先生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地布局、重建,这里讲几个我亲身经历的片段:
一是于先生为了尽快团结和提高全教研室教师的人心和业务水平,提出了每周二下午为全教研室的学术活动时间,每个教师都要轮流作学术报告。我当时刚回到教研室不久,于先生即亲自来实验室问我:“阿宽,你讲什么题目呢?”我说我没有什么好讲的呀。其实,于先生是有备而来,他拿出二篇聚氯乙烯的英文文献给我,说:“你就讲讲聚氯乙烯的合成吧。”
二是在1978-1980年,于先生为了尽快将教师们的专业知识迅速接上并提高到当时的国际水准,主持组织了两本著名的英文学术专著的翻译、出版。一本是R. T. Morrison和R. N. Boyd的《有机化学》第三版(1973),另一本是H. G. Elias的《大分子》(英文第三版,1977)。
是怎么组织翻译的呢?就是把原版专著按章节拆开,每本书都组织了10多位,甚至20多位中青年教师参加,每人承担一二章的翻译,最后由丁新腾、徐积功、于同隐三位先生分别担任《有机化学》一书的一、二、三校,《大分子》一书则由于先生一人校阅。
两本书的翻译,于先生都让我参加了。前面说过,我是大学四年级才开始由俄语转学英语的,再加上后来的荒废,当时的英语水平自己清楚。这样由众人翻译出来的初稿,其水平参差不齐,给后面的统、校者所带来的困难,可想而知。但对像我这样的中青年教师,无疑是一种极大的鞭策和培养。很明显,于先生是通过翻译来培养我们,但他自己要花费很大的功夫来修改审订,可以说真的是让我们趴在他的肩膀上成长。
在1979年10月,中美双边首次高分子学术会议前,中方是作了精心准备的。在当年夏天还先开了个预备会议,请一些主要高分子研究单位去汇报一下可能参加交流的科研成果。于先生就让我和李文俊代表他去汇报。我俩汇报的课题就是“不等活性线型缩聚反应”和“丙烯的淤浆聚合”。在此准备会议期间,王葆仁先生还给了我一个字条,让我也去参加高分子专业委员会会议,旁听他们讨论明年(1980)高分子年会的事宜,回去再向于先生传达。这使我第一次有机会认识了许多中国高分子学科的第一代前辈学者。

1979中美双边高分子讨论会合影,前排左起:于同隐、沈之荃、P. Flory;前排右起:钱人元、王葆仁
1982年4月,美国著名高分子科学家、阴离子聚合的发明人Szwarc教授来复旦访问,并做了四讲系统讲座。那时大家听国外学术报告还有困难,记得是回国不久的江明担任了口译。
值得一提的是,从这次访问开始,我们接待来访知名科学家的方式有了些变化和创新。就是,不仅仅是请来访者作学术报告,我们也举办一个Mini-symposium,由年青老师向来访者介绍我们的研究工作。这在当时是比较前卫的,后来逐渐形成了复旦高分子系的特色传统,并保留至今。这种活动不仅锻炼、培养了年轻老师,为他们提供了与大师面对面的机会,也无形中扩大了复旦高分子,乃至中国高分子的影响力。
我记得那次作报告的有杨玉良、李文俊和我等。我是事先写了讲演稿,给于先生看了,他帮我做了修改。报告后Szwarc还饶有兴趣地逐一作了点评,肯定了我们的工作。
这里想特别说一下杨玉良。他念完初一,1968年底跟随父母下乡务农。1974年作为工农兵大学生,进了复旦大学化学系的高分子专业。那时候非常注重实践,大学生是要经常下厂实习。于先生也到工厂,且与学生们一起吃住。这时他发现杨玉良是棵好苗子。所以杨玉良1977年毕业时,就提议让他留校。紧接着杨考于先生的研究生出了些波折,他专业课都考得很好,政治课差了5分。于先生专门为他写了个报告,说虽然差了5分,但这个学生的政治思想还是可以的。他就顺利进入到于先生门下。从此杨玉良的学习和科研走上了康庄大道。杨玉良后来当选了中科院院士,做了复旦大学的校长。事实证明,于先生没有看走眼,他站在学科发展、布局者的角度考虑问题,慧眼识才,在培养人才方面贡献巨大。
05
1978年,邓小平提出“向发达国家派遣大批留学生”的战略决策。在高分子教研组中,江明、何曼君、王立惠、李善君等先后出国进修学习了。我内心也急切地期待着有出国进修的机会,1982年秋,我向于先生坦露了这个思想。于先生跟我说:“阿宽,不要急。要成立材料科学研究所了,高分子教研室将整体加入。到时我会考虑的。”
1982年11月,材料科学研究所成立,于先生为首任所长。12月份,于先生让我参加学校组织的EPT考试(公派出国留学人员英语水平考试)。通过后,于先生即开始为我联系出国进修的去处。
此时,正好美国麻省大学的Vogl教授接受纽约理工学院的邀请去担任H. Mark教席的首任讲座教授(Mark教授被称为“美国高分子之父”,当时还健在)。当时在Vogl课题组进修的习复(北京化学所)和李善君都快要到期了,需要补充新人。于先生就把我推荐去了。
这样,我在1983年8月,作为Research Associate赴Vogl课题组进修。有了出国进修的机会,内心当然是兴奋的。但心中也很忐忑,我的英语听、说能力,能应付吗?工作上能胜任吗?出国前,向于先生辞行时,我坦陈了自己的焦虑。于先生鼓励我说,英语能力不要着急,有个过程,会逐步适应的,我相信你,工作上努力了,会做好的,还特地嘱咐我注意实验安全等。
到了纽约Vogl课题组,好在李善君、习复被延长了一段时间,和我一起了半年多,所以给了我不少方便和帮助。但具体课题是要自己努力的,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工作,我顺利完成。当年11月,Vogl教授到中国访问,在复旦演讲时,还特意表扬了我。江明很快写信告诉我这个消息。我当然很高兴,紧张的心情也得以稍微放松,在Vogl课题组算是站住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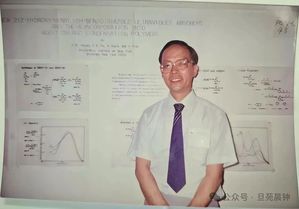
1985年春,府寿宽在美国化学会春季年会上
在当年改革开放伊始,招生、教学秩序基本恢复,师资相对紧张的情况下,于先生高瞻远瞩,大力支持、派遣中青年教师赴西方发达国家学习进修。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复旦高分子学科近三分之二的中青年教师均先后获得了这一宝贵机遇,这个比例在当时是很罕见的。更重要的是这批人均先后返回复旦工作,很多人还开拓了创新性的研究方向,江明、杨玉良后来当选为院士。要知道那个年代出国是要经过层层考核、审批的。高分子专业能有那么多人出国进修,作为领导和“家长”的于先生功不可没。
06
于先生退休后仍然发挥余热,70岁后开创的生物大分子方向,在邵正中等的继续努力下不断创新发展。于先生也一直继续指导博士生,直至2003年,于先生86岁时,他的最后一名博士生姚晋荣毕业。

2003年6月3日,姚晋荣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合影。前排左起:于同隐、姚晋荣;后排左起:陈新、杜强国、颜德岳、章云祥、江明、邵正中、林嘉平
我们复旦高分子的老同事,虽然并不都是于先生的入室弟子,但都以作于先生的学生为荣,对老师满怀尊敬和热爱之情。在先生步入耄耋之年之后,我们经常相约相聚在先生身旁。2000年5月,江明乔迁新居,特别邀请于先生做客,何曼君老师等老同事们一同作陪,共同度过了难忘的美好时光。先生生日和春节,我们也会经常前去拜望。

2000年,于先生和老同事们欢聚于江明家中。前排左起:何曼君、于同隐、吴东棣、江明、李善君;后排左起:董西侠、黄秀云、谢静薇、张中权、鲍其鼐、府寿宽

2014年1月31日(农历正月初一),府寿宽拜望于同隐先生
于先生对复旦大学学科建设方面的巨大贡献,学校领导是有高度评价的。记得在1990年代初,时任副校长杨福家曾对我们说:于先生是全校培养博士最多的导师,我们要好好尊重先生。于先生75岁、80岁、90岁大寿,我们都怀着对于先生由衷的尊敬和热爱,为其举办了庆贺活动。80大寿时,时任校长杨福家特地出席。特别令人难忘的是,2016年6月21日,于同隐先生的跨越60多年的几代学生们齐聚一堂,为先生庆贺百岁大寿。欢声笑语,盛况空前,堪称可载入史册的大事。

1997年9月16日,杨福家校长祝贺于同隐先生80华诞

于同隐先生百岁华诞庆祝大会合影
07
于先生是我国高分子学科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复旦大学高分子学科的创始人、布局者,也是我们这辈人共同的导师。于先生在学科建立之初就从大局出发,在复旦逐步建立起健全的高分子学科体系。他自然不可能在所有领域为大家提供学术上的具体指导。但他对我们给予充分的自由、信任,将自己的研究生、博士生放手给年轻教师带。这一点江明、杨玉良和我等是直接受益者,我们都是在还没有博士导师资格时就担负起带博士生的责任。此外,早年都是于先生亲自到外边接课题、项目,筹集经费,然后放手让年轻教师去做。但在发表论文和评奖时,他都是不署名的。他曾有形、无形地帮助很多同事、学生解决了大问题,但事后大家向他提及的时候,他总是说“有吗?我不记得。”
作为老教师,我很高兴地看到,复旦的高分子1993年独立建系,有三位中科院院士,十几位杰青、长江,系友中的杰出人才更是数不胜数。我认为复旦高分子学科之所以能有今天这么欣欣向荣的发展态势,于先生谦虚、淡泊、宽厚、平等待人、甘为人梯的善良品格,勤奋努力,以身作则,以身为范的实际行为,和由此所形成的学术民主、宽松自由、努力奋进的优良学风,是最为重要的因素。更关键的是,这种学风被于先生的后辈同事、学生和复旦高分子人所继承、发扬。
2022年高分子科学系以研究生培养的“于同隐模式”获教委教学成果一等奖。
2023年5月,于同隐铜像落成仪式在复旦大学江湾校区高分子科学系大门前隆重举行。铜像由于先生的学生和同事自发捐款筹建,以为永久纪念。

于同隐先生铜像落成揭幕仪式
来源:旦苑晨钟公众号
鸣谢:江明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