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充分体现我校老教授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进一步推进老同志在当前“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背景下发挥作用,2019年,我校设立了老教授课程思政工作坊。在老干部党委的统筹下,由老干部工作处牵头负责,联合退休教职工工作处、教务处、党委教师工作部等部门,共同推进老同志参与学校中心工作。2020年,工作坊联合《复旦》校刊,开设“老教授谈教书育人”专栏,特邀各院系老教授结合多年来教书育人的经验,围绕“我所开设过的课程”、“我当年是怎么编写教材的”、“我当年是怎样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的”、“我们当年是这样备课的”等主题撰写文稿,传授经验为主,讲述当年故事为辅,为广大在职教师备课、教学、教材编写等方面提供借鉴和参考。
百廿复旦正青春,教书育人薪火传。“老教授谈教书育人”专栏系列文稿,既在《复旦》校刊定期发表,也在《校史通讯》和复旦主页“相辉笔会”刊登,并陆续在“旦园枫红”公众号加以推送,通过个人回忆与历史见证,展现120年来的复旦故事、师德传承和教书育人的温度。本期与您分享熊庆年老师的编书心得,并借此对熊老师表示敬意和谢意。
《复旦大学教育学科史稿》撰写一得

熊庆年
1954年2月生,江西南昌人。中共党员,教育学博士。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原所长,《复旦教育论坛》原执行副主编。曾任复旦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长、教师发展委员会委员。
初心不改乃有动能
记得2005年,复旦大学百年校庆时,校庆办安排由高等教育研究所接待原教育学系的校友。我原本以为不会有教育学系的校友来寻根,后来才发现自己错了。先后有好几位年过七旬的校友找上门来认亲,让我仓促之中应对失据。由此,我萌生了为教育学系写史之意。因为要让前辈们找得着家,不把历史弄清楚,那是不可能的。

1934年春,复旦大学教育学系系友会合影
教育学科相对而言是不成熟的学科,不成熟的学科可以写史吗?在学科走向成熟的道路上,记录下其曲折起伏的发展历程,描绘出其成长的轨迹,或许更能彰显学科史面向未来的价值。教育学科的发展史,从某个侧面也反映了大学的发展史。以复旦大学为例,其教育学科史的特殊性在于,历任校长对这个学科多有青睐,投入了比其他学科更多的心血。在民国时期,李登辉校长对教育学科发展的谋划、推动,可以说不遗余力。吴南轩、章益两位校长也对其关怀备至,亲力亲为。
做足功夫方能成事
我硕士专业是汉语史,博士专业是教育史,也许有“史”的专业基因,很早就有整理所史的想法。我退休后就打算把这件事做下去。
2020年6月22日学校党委宣传部和档案馆发出《关于复旦大学院系(学科)发展史项目申报的通知》。正中下怀,看到后立即起草了申报书,得高国希所长支持,上报后即得批准。有学校的项目支撑,我自然信心百倍。又找到接替我开“高等教育史”课的李会春老师,请他协助。他二话没说,一口应承,并组织上“高等教育史”课的硕士研究生先干起来。
一年半过去,形成的稿子离理想目标差得很远。之后决定亲自下场。与李会春达成共识,他负责1952年前教育学系部分的撰写,我负责高等教育研究所部分的撰写。然而,一摸史料,才知道工作量巨大。李会春负责的那部分,查找民国档案资料就是个极为艰难的活儿。而我负责的这部分,也是让人挠头皮的事儿。杜作润老师留下了一纸袋资料,过去没有认真地翻过,现在打开仔细一看,才知并非系统的档案资料,更何况时间久远,有的已经字迹难辨。遗憾的是,杜作润老师已经故去,很多史实无法确认。
我和李会春专门去拜访了老所长强连庆、孙莱祥,求证一些大事。因为他们年事已高,一些记忆也已经模糊,书中尽可能利用了他们的访谈材料。我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第三任所长蔡达峰,他过于自谦,表示“这个时期高教所的发展成就,是全所同志的共同努力的结果,见证了学校的发展进程。本人作用甚微,乏善可陈”。早期资料散失情有可原,然而,我担任副所长、所长的近20年,资料也散失不少,深深自责。我花了一年多工夫,把幸存的材料全部用扫描仪电子化。搜集和整理材料所花的精力和工夫真是一言难尽,更伤神的是如何把得来的材料连缀起来。起先有个全书的整体框架,但实际写起来,才发现处处扞格。框架调整了一次又一次,草稿写了一遍又一遍。幸得李会春不厌其烦,陪着干。也幸得所里同事们不嫌我叨扰,帮助翻找陈年旧账,总算勉强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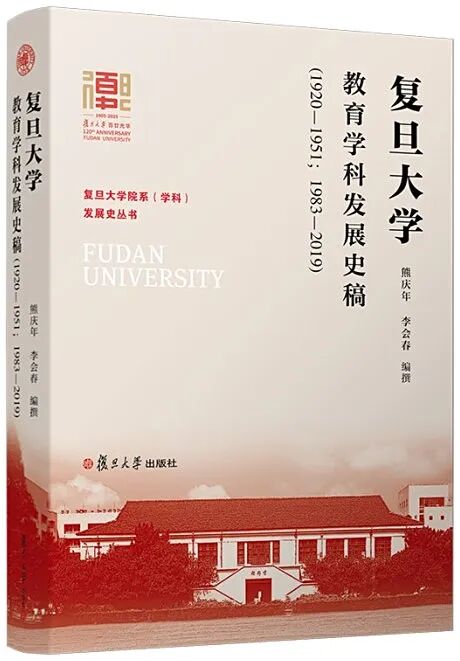
书之所以题名为“史稿”,就是因为还十分粗陋,离心目中的样子依旧差很远。再者,有些事情可能只有让后人来写恰当,自己写自己经历的事恐怕难保客观。还有些事多少有些敏感,不便于展开,曲尽其笔,语焉不详,可能让读者雾里看花。学术发表方面,多记流水账,未厘流变,非不愿投入,乃不能也。或许需要时间的沉淀,方能看清眉目。所以,反复多次,最后搁笔一点也不觉得轻松。全书最后由我统稿,不当之处,皆我之责。
追求真实才会靠谱
《复旦大学教育学科发展史稿(1920—1951;1983—2019)》出版样书收到后,我寄了一本给“人民教育家”于漪,她是复旦大学教育学系最后一届毕业生。96岁的于老师尽管体弱多病,但脑子依旧好用。她给我打了十多分钟电话,听得出,她异常兴奋,连声说,“太好了!太好了!”因为有教育学系的“家谱”了。

2005年6月高等教育研究所教师探望于漪老师
我的同事徐冬青说,这本书“为我们复旦高教所留下了印迹”。想必日后教育学科发展得更好了,回头再看看走过的路,就会知道我们从哪儿出发的、为什么出发;走了多远、走了多高。
老校长王生洪读到《复旦大学教育学科发展史稿(1920—1951;1983—2019)》后,给我发了455字的短信,指出:“粗读之下,深感这部史稿得来不易——您将复旦教育学科的历史清晰追溯至1920年办学早期,又完整梳理了其后的曲折历程,让学科今日的扎实根基更显珍贵。”“我在职期间,早已见证高教所的卓越作为:不仅在教育学科建设、学术研究与人才培养上步履不停、成果丰硕,更主动为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学科布局规划、长远发展谋划等工作深入调研、建言献策,提供了扎实的咨政服务。我感到这部史稿也填补了全面论述复旦教育学科发展史的空白,既能为教育学科未来发展提供镜鉴,也让更多人得以深入理解复旦大学的教育文化底蕴,很有意义。”

2000年秋,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师合影,从左到右:林荣日、张晓鹏、周洪林、孙莱祥(副校长兼所长)、杜作润、熊庆年
“书中提及学校筹备成立教育学院的往事,距今已二十年,读来令人感慨。犹记当时您为此事投入极大热情、倾注诸多心力;如今恰逢复旦建校120周年,学校重提这一设想并纳入计划,实在是令人振奋的好消息!”老校长的勉励,不禁让我为之动容,思绪万千。
为后来者鉴是目标
整理复旦大学教育学科的发展史,直接的目的是梳理学科发展的脉络,保存历史的记忆,更高的目的是认识复旦大学教育学科发展的规律。然而,规律是个非常难触摸到的存在,而且就一所大学的教育学科百年来考察也未必就称得上是规律。但是无论如何,还是得有点反思,以为后来者鉴。
第一、理性克服外部环境的消极作用。外部环境对教育学科发展有时是决定性的。复旦大学教育学科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初发生了中断,空缺了33年,这是政策大调整所形成的,是不以学校和教育学科共同体的意志为转移的。此处不论是非曲直,唯陈客观事实。一旦中断,要接续起来,那是非常困难的。重起炉灶事实上比新起炉灶还要困难。因为中断,实际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已经造成了教育学科可有可无的成见。恢复首先就会遭遇教育学科存在的必要性的拷问。在高等教育研究所成立之后的30多年间,始终面临着这种拷问。
第二、除了大的外部环境,在学校范围也有教育学科的外部环境问题。在各种环境因素当中,大学领导层的认识是最为关键的。1952年前教育学科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实赖李登辉校长的明鉴、智慧,以及后之校长吴南轩、章益的努力,才使教育学科薪火相传、弦歌铮鸣。改革开放之后,曾几何时,几乎每个大学都有一个高等教育研究室或高等教育研究所。30多年过去,仔细审察一下,就可以知道“几家欢乐几家愁”。那些发展壮大的,无不是得到大学领导鼎力支持的。那些灰飞烟灭的,基本上都是被大学领导视之如草芥、弃之如敝履。
第三、外部环境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强大学科给弱小学科造成的一种无形的压迫。大学是一个学术共同体,它是一个系统性的结构,学科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一种竞争关系。在日益利益化的学科生态环境之下,学科形成了一定的等级,这些等级转化为一定的话语权,影响着学科资源的配置、学术质量的评价、学术群体的权益甚至组织的存续。高等教育研究所自诞生之日起,就处在一种紧张的学科关系之中,小心翼翼是必然的,不得不努力借助各方的力量。这就涉及学科自身对外部环境的认知。大部分外部环境的因素是无法改变的,但我们如何去改变自身,适应这种外部环境,克服不利的环境因素,甚至部分改变环境,需要清醒的战略考量。不管怎么说,无论教育学系时期,还是高等教育研究所时期,总的走向是从弱小到壮大的,是不断发展的。主观能动性,就表现在克服困难、努力奋斗之中。
探索规律至关重要
教育研究,尤其是高等教育研究,关注理论还是关注问题的争论一直未消停,过段时间就会冒出来。强调关注理论者认为,高等教育研究应聚焦于理论构建,以形成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通过对高等教育现象、规律等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究,为学科发展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理论研究能够为高等教育实践提供前瞻性的指导,研究者通过理论分析和逻辑推理预测高等教育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可能出现的问题,为实践提供方向指引,避免实践的盲目性。注重理论研究有助于提升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地位和价值。通过严谨的理论论证和学术创新,推动高等教育学科的学术发展,与其他学科进行对话和交流,争取在学术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强调关注问题者认为,高等教育学是应用性的学科,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解决现实中的教育问题。关注问题就是关注实践的发展。知识来源于实践,高等教育研究应紧密结合实践,从实践中提炼知识和理论。实践中的经验和案例是研究的重要素材,通过对这些素材的分析和总结,能够生成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的知识。实践研究能够直接推动高等教育改革的进程,研究者通过参与教育改革实践,了解改革的需求和难点,为改革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使改革能够顺利进行,从而体现它的价值。
两种观点各有轩轾,实际上是一个如何把握两者关系的问题。就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经历而言,总体走向是偏重问题研究、实践研究。无疑这种偏向是由于现实语境的条件约束,也受组织发展功能实现条件的限制。只能从此时此地、彼时彼地的实际条件去作决断,但这绝不是倡导机会主义,而是需要有长计划、短安排的智慧。在特定语境下把握好问题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关系,确实非常重要,而且不是简单地平衡所能解决的。
院校研究是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实际上是一个舶来品,源自美国。仔细考察美国院校研究,具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以数据为基础,二是围绕学校经营,以学生消费者视角为中心。我国高校高等教育研究机构的转型,不应仅仅停留在组织功能的选择层面,更应实现研究范式的迭代,即从我国高校的实际出发,服务学校的改革与发展。从广义角度看,围绕学生发展开展研究,并通过数据分析为决策层提供参考,无疑是重要的。但研究议题和内容不应仅限于此,大学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国际交流等功能,皆可纳入研究视野。院校研究本质上是为领导决策服务的,领导的重大关切就是其研究任务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近40年的服务,值得回味、深思。
本书写作的一个着墨点就是学科发展的机遇。机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发展的机遇对一个组织而言,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复旦大学教育学科发展的历史就是这样。在教育学系时期,李登辉校长对社会发展教育需求的判断是高屋建瓴的,对章益赴美留学方向的指引是独具慧眼的。复旦大学教育学科的前程差不多在那一刻就谋定了在高等教育研究所时期,教育学院筹建、搁置的过程,以及数年后再次被提起的过程,回想起来,令人扼腕也就在特定的时机,甚至是某个人物、某个细节。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一挥即逝。说起来是一种偶然,仔细琢磨又是必然。关键人物的思想境界、处置和决断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历史没有如果,不会重来一次。
教育学科、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是一个逐步成熟的过程,需要不断积累和反思。发展教育学科是长线的事业,在“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思维框架下,长线的事业很可能被抛弃。因而,是做小还是做大?做完整的教育学科还是只做二三个二级学科?发展教育学科不仅面临外在的拷问,而且面临内在的自问。不管怎么抉择,有一点大概是可以确定的,在复旦大学这样的学校里,教育学科的发展必须扎根现实土壤,摒弃纯书斋式的学问。
复旦大学教育学系诞生过百年了。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诞生有四十年了。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此情可待成追忆,其意犹堪寄远山。再过五十年、一百年,也许人们就能洞悉其规律了。
本文转发自复旦大学出版社公众号,标题和小标题经作者修改。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