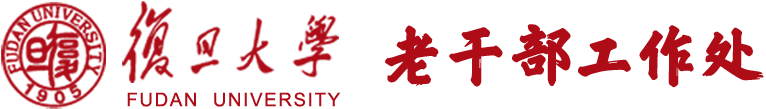为充分体现我校老教授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进一步推进老同志在当前“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背景下发挥作用,2019年,我校设立了老教授课程思政工作坊。在老干部党委的统筹下,由老干部工作处牵头负责,联合退休教职工工作处、教务处、党委教师工作部等部门,共同推进老同志参与学校中心工作。2020年,工作坊联合《复旦》校刊,开设“老教授谈教书育人”专栏,特邀各院系老教授结合多年来教书育人的经验,围绕“我所开设过的课程”、“我当年是怎么编写教材的”、“我当年是怎样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的”、“我们当年是这样备课的”等主题撰写文稿,传授经验为主,讲述当年故事为辅,为广大在职教师备课、教学、教材编写等方面提供借鉴和参考。
“老教授谈教书育人”专栏系列文稿,既有在《复旦》校刊定期发表,也有在《校史通讯》和复旦主页“相辉笔会”刊登。我们将在本公众号中陆续加以推送。本期与您分享江明院士的教研心得,并借此对江院士表示敬意和谢意。
江明 196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历任复旦大学化学系助教、讲师,复旦大学材料系讲师、副教授、教授,高分子科学系教授。1979-1981年英国Liverpool大学访问学者。200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2009年当选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曾任《高分子学报》等多个国内期刊编委和《Macromolecules》等多个国际期刊顾问编委。聚合物分子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011,2003)、Polymer冯新德奖(2011)、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1996)、二等奖(1989)等多项奖励。著有《高分子合金的物理化学》、《高分子科学的近代论题》(编著)及《大分子自组装》(合著)等书籍。
我在复旦的学习生涯
我是于1955年入复旦大学化学系学习的。在大学的授课老师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吴征铠先生。1957年,先生为化学系大三学生开设课程《物理化学》,这是我最喜欢的课程。吴先生是留学英国剑桥回来的知名教授,讲课时家乡乡音很重,由于我和他是同乡,故我听他讲课十分亲切,听课很认真、很享受,真想把一字一句都记下来。我的这本笔记还有个小设计,除了记录老师课堂讲授内容,每一页都留了空白部分,用来记录我自己在课下思考消化和查阅资料的心得体会。这本笔记是我的宝贝,珍藏至今已60多年了。
吴征铠先生《物理化学》一课的课程笔记

江明院士的学习笔记
1958年夏天,我在复旦大学化学系刚读完大学三年级。暑假开始,我就接到任务,协助北京化学所钱人元先生一行到复旦来开办“高聚物分子量测定训练班”。我的任务是和系里几位老师一同准备训练班的几个实验,也算是一个小助教。训练班开始,我就有幸随学员一起聆听了先生的全部讲课。讲课持续约一周。钱先生的系列讲课是先生带领施良和、程镕时等学长白手起家建立起的全套分子量测定方法的精华。那时钱人元先生年方40,风华正茂,讲课从容潇洒,无论是艰深的光散射理论或是繁琐的渗透膜的制备,他给我们的是清晰的物理图像和操作背后的原理。我听课前几乎不知高分子为何物,但这一星期的课程使我如浴春风,对高分子这门新兴学科可谓一见钟情,对先生更是不由心生崇拜之情。也许是因我那时当小助教表现良好,训练班结束后不久,我就被选中了提前本科毕业,随于同隐先生,边干边学,参加到复旦大学高分子学科的创建中了。所以说,我和钱先生真是有缘,是钱先生来访办班这个偶然的机会,引导我走向了高分子的科学之路。不久以后,钱人元先生著的《高聚物的分子量测定》一书在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是当时国际上也未见到的全面论述高分子表征的著作,以后被译为俄文和英文出版。在该书出版后的几年中,对于我和在复旦大学从事高分子溶液研究的几位同事来说,这本书成了我们工作的“圣经”。 1960年江明院士在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钱人元先生实验室学习仪器研制的笔记

1963年钱人元先生在上海作高分子物理系统讲座,图为江明院士的听课笔记
1960年暑假,我手持于同隐先生的介绍信到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面见钱先生(他们是浙江大学的同窗好友),要求在他的实验室学习两周。在钱先生办公室,他对我这无名后辈十分和蔼地说:“欢迎欢迎,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我忐忑不安的心情随即放松了下来。在钱先生的实验室的那两周,我真是如鱼得水,不但仔细学习和操作了光散射仪,还详细纪录了钱先生实验室正在研制中的应力松弛仪、介电损耗仪的设计方案等等,可说是满载而归。回到学校后我们改建了自己的光散射仪,终于开始获得了可用的数据。1964年,基于这台仪器上的工作,我们的第一篇论文在《高分子通讯》上发表了。事实上,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钱先生的指导下中科院化学研究所已建成包括谱学、溶液、力学以及介电等等的综合性的高分子物理和物化实验室,这在当时国际上都是少见的。
海外访学赤子心
我从1958年开始科研教学生涯,但并非一帆风顺。上世纪70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带来了我人生命运中的大转折。在之前,我从没想过自己能够出国学习,1978年接到准备公派出国学习的通知,1979年春去英国Liverpool大学留学。 Liverpool大学有很好的高分子的传统,是很优秀的。因为我们是公派出去的,所以那边的教授还是欢迎我和他们一道工作,至少是一个劳动力。当时有两位老师都希望我跟他做,一个叫Bamford,是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FRS) ,非常知名的一位教授。他有一本书著作“The Kinetics of Vinyl Polymerization by Radical Mechanisms”,我在出国以前就读过的。他在自由基聚合方面是权威,他的文章在不断的发。还有另外一位是Eastmond,以前是Bamford的学生,后来他有了自己的课题组。但他的重点转到Multicomponent Polymers, 就是多组分聚合物,当时这个是一个新兴的方向。就是把多种聚合物放在一起,看它的物性,看它的结构与性能的关系。我做了一些比较,如果跟Bamford,发文章是没问题的。但从学科上讲,当时他的方向基本的内容已经确立,很难有比较大的发展。由于国内已有很多人在这个领域工作,故将来回国后,也难有大的贡献。而多组分聚合物,虽然很不成熟,导师的名气也不是很响,但是我觉得可能会学到一些很实际、很有用的新东西,有助于回国开展工作。所以我选择了Eastmond。今天回想这件事,我觉得还是做了一次很正确的课题选择。我在二十岁的时候就提前毕业,但作为一个大学教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过了二十多年我才有机会,安下心来从事真正的科学研究,所以我是多么珍惜这个机会。刚开始的时候,我的英语还不够好,为了锻炼听力,我用卡式录音机录下BBC每天播送的世界新闻提要,五分钟的内容翻来覆去听上两个小时,并记下来,没听清的再翻阅字典反复推敲。自备的卡式录音机无法清晰录下老师的讲课内容,就拜托管理教室的教务员用无线话筒录音,课后反复温习。这样两年下来,我的英语水平大幅提高了。在国外的两年,我真是“如饥似渴”,学理论,打基础,做实验。然后到了1981年的春天,也就正好是我出国两周年的那一天,我就回来了。回国后,因为当时大多数教师和同学都不能听懂英语报告,我就担当起许多国外专家报告现场翻译的任务了。

1980年江明院士在Liverpool大学NMR实验室
我同事中好多人都知道我以前曲折的经历,故以为我不会回国了,但我还是回来了。我觉得,做人一定要有诚信,既然当时做了承诺,就应该兑现,这是我一直遵守的原则。做科研也是如此,诚信为本。时常有人问我,当年回国是否曾心存犹豫?回答很简单,没有。这也不值得夸耀,而是很自然的选择,国家送我出去学习,我就应该回来。科学无国界,但科学成果是有国籍的。我从事了一辈子科学研究,最骄傲的不是成为院士,不是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而是我的每一项成果都打上了中国的标志,是“中国制造”。
科研工作的幸福之源
从1979年开始做科研,至2018年退休,前后四十年,总体来讲我是很乐观的,过得很愉快的,精神上很享受。这主要有三个来源: 第一,我充分享受到自由选题的乐趣。在复旦,课题选择完全是由我按照自己的意愿定的,也就是curiosity-driven,完全由“好奇心”驱使去做,从深究问题的科学内涵来提练出问题,去寻找自己想做的问题,并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这是最愉快的事情。不过,可能会有人问,这样,大家不都只想做这类研究,不想去去企业里去从事研发工作了吗?其实事情不会这样。这里牵涉到很多得和失的关系。是的,我们是充分享受到自由选题的愉快,但同时,我们也要失去一些东西。例如,与同资历的人相比,在工业部门从事研究开发,收入要比我们多得多。我的学生,即使是刚获得博士学位的,如找到好的位置,收入也比我要多,在国外情况也是如此。但在那些单位工作,选题是没有这样的自由的,他们从事的研究由市场决定,由领导决定。很急的时候,可能要加班加点把某项研究赶完,但是一旦发现市场不再需要了,老板也许会要求你明天就必须把它停掉,哪怕你对这个课题再有感情,你也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所以,我们在这之间可以做取舍。同学将来毕业择业就要考虑到这一点。如果你对研究工作,对基础研究,真的有兴趣,在“业余”时间你愿意投入更多,那么你来做,就会得到很多幸福,但同时你也要准备失去很多东西。作科学研究是“没完没了”的,各种需要和新问题不断的出现,迫使你不断地学习。

1988年江明院士参加IUPAC Macro大会
第二,快乐还来自于所谓的成就感。我从小性格就不爱随大流,别人一哄而上的事情我很少跟风,有时会在一边冷静看着,独立思考。我还记得小学四年级时候的一件小事情,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那时“自然”课老师上课在讲台上演示动滑轮和定滑轮,然后问同学们有谁想上台去亲身体验拉一下滑轮,同学们全都举手,为让老师挑上自己,甚至纷纷站了起来。我当时想,个个举手不等于都不举手吗,于是坐着没动,只是眼睛盯着老师。可能这样我就变得特别显眼,老师还真的点中了我!以后多年的实践使我坚信,从众心理有时并不可取,独辟蹊径才有出息。事实证明,这一思路在科学研究中是宝贵财富。我始终认为科学研究需要具备高度的敏感性和鉴别力,不要轻易放过细小的疑点和异常,一些未曾预料到的疑点问题,可能触发一个新的重要生长点。
1995年钱人元先生和江明院士在第一届东亚高分子大会上(上海)
有一次,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使用传统“荧光探针”无法测试“含碳氟链水溶液的高分子”这一难题。当时的我就想:这一预料之外的“失败”会不会孕育着新的发现?经过大量试验,我们果然用化学法改进了传统探针,发明出针对此类高分子的“靶向荧光探针”。成果发表在著名科学杂志《大分子》上,审稿人的给出了 “it is hard to criticize such a well-written and clearly presented paper.(对写得如此好和表达清晰的文章提出批评是困难的。)”的罕见评语。后来这篇文章被广泛引用,“靶向荧光探针”在法国和日本的几个实验室都用得很成功。我们当初知难而上,虽然平添了几分辛苦,却收获了更多的创造乐趣。

江明院士在2010年IUPAC世界高分子大会做大会报告
再有,我想我的快乐还来自于真诚的合作。我们有好几次很成功的合作,包括早期在均聚物和共聚物的相容性方面,我们和东华大学(原中国纺织大学)谢涵坤老师的合作。他是搞理论物理的,我们一起来解决共聚物和均聚物相容性的一些理论问题,在八十年代后期就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对水溶性高分子疏水缔合问题,我和章云祥教授合作且在物理和化学方面做了一些分工,合作也是非常的愉快。跟吴奇院士的合作就更多了,前后有十多年,我们合作的一部分内容得到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很有趣的是,我们合作很多年,但是我们并没有一个联合申请的课题,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课题是共同享有经费的。但是我们有共同的兴趣,它驱使我们在一起来作研究,我们从来没有为成果的分享产生任何的隔阂。俗话总说“文人相轻”,但我欣赏、我崇尚“文人相知”。大家相互理解,互相帮助,这是构建和谐科研生态的基础。
最后我要说,愉快的心情还来自我的学生们。几十年来,我培养了近百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这么多的同学,他们的能力是有高低的,性格也有差异。但总体上他们都是一些优秀的青年,大家都有一种很强烈的愿望到复旦来学习,走科学的道路,所以是一个优秀的群体,我理解他们。和他们朝夕相处,同学会不断地提出科学上的问题,我们一起去探讨,去解决,对我来说,也是不断学习的过程。跟同学们共享研究的成果,确实是非常愉快的事情。我退休多年了,住养老社区,不断有过去的学生来看望,其中有许多人在工作上取得杰出成就,经常带给我科研上的好消息。他们中年长的已经退休,最小的还在国外读博或做博士后,见到他们我总是特别高兴。看到我这里经常宾客盈门高朋满座,邻居朋友们都很羡慕。
江明院士与课题组成员
我为什么能保持快乐,最根本的一点,那就是,我见证了我们国家这30多年的巨变,伴随他从深渊中挣扎出来,一步步迈向光明。见证了我国的化学研究从世界垫底到今天成化学大国,也为此流了汗水,这是真正的幸福之源。
对于青年的寄语
我还记得开始第一次做课程实验的时候,老师讲:“如果你在笔记本上写了数据,你发现有误要更改的话,你不可以用橡皮擦掉它重写,你必须用笔把错的地方划掉,把正确的写在旁边,留一个真正原始的记录。”这使我明白,对于实验结果和数据,要有敬畏之心。理科生的专业学习是学习自然科学,但是他毕竟是一个社会的人,他学到的知识是要为社会服务的,所以他具有什么样的人生观点,什么样的人文情怀,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在我们今天公认的我国第一代杰出高分子学人中,除王葆仁先生和钱宝钧先生年长些外,冯新德、钱保功、于同隐、钱人元、何炳林、杨士林、徐僖、黄葆同等先生(以出生年月序)都出生在1915-1921这七年间。他们都是在上世纪30-40年代日寇侵华,国家处于危难之际完成他们的大学学业的,历史造就了他们崇高的爱国精神和坚毅求真的学术品格。从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30年中,他们在完全与西方发达国家学术界隔绝的环境下,从无到有地创建了我国的高分子学科,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分子人才队伍。期间虽经历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的干扰和破坏,他们拳拳爱国之心,始终不渝,为我国的高分子学科打下了较坚实的基础。在改革开放后的十多年中,他们又带领后辈完成了学科复兴。本世纪初,我国的高分子学科终于走上了快速健康的发展之途。我们的前辈的爱国情怀和坚毅不拔的学术求真的精神,是值得我们代代相传的。
欢迎继续关注 “老教授谈教书育人”系列推送
文稿整理:郭福英
文稿审核:江 明
编 辑:韩 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