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充分体现我校老教授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进一步推进老同志在当前“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背景下发挥作用,2019年,我校设立了老教授课程思政工作坊。在老干部党委的统筹下,由老干部工作处牵头负责,联合退休教职工工作处、教务处、党委教师工作部等部门,共同推进老同志参与学校中心工作。2020年,工作坊联合《复旦》校刊,开设“老教授谈教书育人”专栏,特邀各院系老教授结合多年来教书育人的经验,围绕“我所开设过的课程”、“我当年是怎么编写教材的”、“我当年是怎样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的”、“我们当年是这样备课的”等主题撰写文稿,传授经验为主,讲述当年故事为辅,为广大在职教师备课、教学、教材编写等方面提供借鉴和参考。
百廿复旦正青春,教书育人薪火传。“老教授谈教书育人”专栏系列文稿,既在《复旦》校刊定期发表,也在《校史通讯》和复旦主页“相辉笔会”刊登,并陆续在“旦园枫红”公众号加以推送,通过个人回忆与历史见证,展现120年来的复旦故事、师德传承和教书育人的温度。
数学是学好计算机的基础

吴立德
中国最早从事计算机视觉和自然语言处理研究的科学家之一。1937年生,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纽约科学院院士,中文信息学会会士,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视觉专委会(CCF-CV)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的早期推动者之一。曾任复旦大学首席教授、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系主任、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多年来在这两个领域培养了二十余名博士、六十余名硕士。在概率论、计算机视觉和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吴立德教授一共出版了七本专著,发表了两百余篇论文。完成了近五十项科研项目。吴立德教授是复旦大学人工智能研究的创始人,开创了复旦大学计算机视觉和自然语言处理两个研究方向。1982年,吴立德教授在人工智能顶级学术期刊《IEEE Transactions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TPAMI)上发表了中国大陆学者的第一篇论文。1990年起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获上海市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和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词典·当代人物卷》等名录中,吴立德教授均以学者身份名列其中。2018年,吴立德教授获得中国计算机学会计算机视觉专委会(CCF-CV)终身学术贡献奖。2021年,入选中国中文信息学会会士。
搞计算机的一定要把数学基础打扎实
我是1955年进复旦的,先是在数学系。本来是四年制的本科,我们这届就改成五年制了。那个时候需要一部分学生提前毕业留校,所以我留校了,研究概率统计。开始最先接触的项目来自上海水文地质大队他们有些数学问题,就找我们数学专业的解决。一接触到实际,就发现项目需求跟我们学校里的研究确实是不一样,需要面对大量数据,然后根据大量数据做一些统计和分析,就在那个时候我接触了计算机。
1975年,学校成立计算机科学系(地点就在现在的袁成英楼),那么我们就从数学系过来。整个计算机系大概三分之二的教授是从数学系过来的,三分之一是从物理系过来的。所以,真正有计算机系大概75年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做了一些数学的应用,都要用到计算机的。当时全国建计算机系,基本有两种模式。像复旦这样的文理类综合大学,基本由数学系和物理系的老师结合起来形成一个计算机系。建系初期,大概三分之二的老师是从数学系过来的,三分之一的老师是从物理系过来的。物理系偏重搞硬件,数学系偏重搞应用和软件。像交大这种工科学校,他们一般从电子工程系、自动化系那类的系中分出计算机系来。我们比较成功的就是做了这两件事情,一件是上海的地面沉降问题,还有一件是用地震方法探测石油的问题。这个就比CV要早了,当时还算是属于信号处理还没到图像(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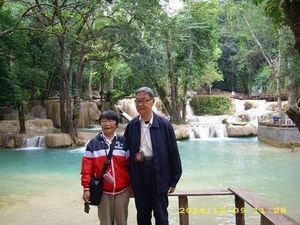
吴立德教授和爱人吴霭成教授
计算机编程,是语言的问题,是怎么和计算机交流的问题。现在的编程语言,已经演变成编程环境了,在编程环境中编写代码。但是怎么将实际问题用数学办法解决,这其实是比代码实现更加难、更加重要的东西。这些都涉及高等数学。当年我们研究上海地面沉降和地下水的关系,要考虑获取哪些数据,怎样通过计算机处理这些数据,看看是不是符合实际。这些用手算显然不行。在实际应用的时候,特别是牵涉到大数据量的时候,第一用数学方法把关系找出来,第二用计算机执行,看看对不对。如果你是想要一点创新,你没有一定数学基础是很难的,你会编程,那当然也可以,但是你真正要想有些新的东西出来,没有数学是不行的。
教学与科研是相辅相成的
现在好多教授上课都用PPT,一沓一沓打上去,但是牵涉到一些数学上的东西,你一张纸头打上去,其实不是很好理解的。如果你板书的话,就一步步推导下来,一步步有个过程,会很清楚的。我讲课其实自己是要写一遍的,是要背下来的。
我们的老师苏步青先生曾说过:科研和教学一起做是最好的。如果专门做科研,科研有时候做得顺利,有时候做得不顺利,那你可能很长一段时间做不出结果出来,人就会很懊丧。教学的话,你就是在讲课。所以你两方面做,既做教学又做科研,科研如果有点心得的话也可以放到教学里面。然后做教学的话,你也会对你过去学的东西有些更深入的了解。有时候你读书,对于一些问题并不是很了解或者说不是很透,然后你教的时候就能弄得清楚点,不然学生一问就把你问倒了。所以说教学和科研实际上摆在一起是最好的。为人需要把本职工作做好,与人相处坦诚;为学需要打好基础,循序渐进,巩固并系统化学过的知识;为师即为人师表,教书育人,为学生指引方向,给学生较好的环境,在具体问题上和学生讨论并给予指点。

左图为吴立德教授备课期间手写的推演笔记,右图为吴立德老师在上课
做科研需要循序渐进,同时也要敢于提出自己的想法
巴浦洛夫对青年人搞科研提了三条,我觉得很好,一个是循序渐进,搞新东西前要把基础打打扎实,一个是要热情,要做好的东西确实不容易,会碰到很多挫折,花费很多时间,没有热情也不行的;还有一个就是要谦虚,不然稍微做出一点成果就满足了。这三点我觉得确实是很重要的。巴浦洛夫的文章很短,网上都能找到。很多有价值的工作都是下了几十年的功夫,要坐得了冷板凳,能够坚持,是很重要的。得诺贝尔奖的人都是对这方面感兴趣,对研究感到乐趣,自己做这件事本身就很高兴。有些孩子,家长要他去弹钢琴,他觉得很痛苦,这就不行了。能做出好工作的人,他本身就是感到做这件事情本身的乐趣。好的工作肯定是要积累的,当然要靠本人的坚持,也靠社会的环境能够允许这个人去坚持。无论是搞理论也好,搞应用也好,要做出很好的工作哪有那么容易,肯定要长期坚持,在做的时候自己也感到蛮开心,这样才行。有些人觉得看电影是开心的,有些人解出一个问题就高兴得要命。要做得比别人好,总要付出多一点。个人长期的努力比天资更加重要。也不见得生活就枯燥得难以忍受。如果努力了,做出的成果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承认,这种喜悦不见得比看一场戏、看一场球来得逊色。只要有兴趣,把兴趣投入到学问中,就不会累了。我不是那种喜欢开夜车的人,睡眠时间还是保证的。关键是要想办法提高效率,光拼时间是没什么意义的。

左图为吴立德老师获2018年度CCF-CV终身学术贡献奖,右图为2021年12月18日,中国中文信息学会(CIPS)第九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学会成立40周年学术年会于北京举行。吴立德教授入选中国中文信息学会会士。该称号旨在表彰中文信息处理领域做出突出贡献并取得卓越成就的科学家。
华罗庚先生说,解决数学问题就像是抓住一个兔子,最大的本事是知道哪里有兔子,然后去把兔子抓住。发现兔子,发现问题,比你去抓兔子还难。如果不知道哪里有兔子,要怎么抓呢?要找到一个好题目还是不容易的。社会环境也要允许年轻人讲出一些自己的想法。
有一个报道说,Nature上发的,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针对这四个国家的计算机专业和电子工程专业的大学生做了大规模的测试。分成精英大学,相当于中国的985、211,一般大学,用同样的题目对这四个国家的学生进行测试,包括数学能力、物理能力等等,测试三次,一次是大学入学的时候,第二是两年以后的测试,最后是四年以后的测试。结果发现,美国大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比其他三国都好,中国学生的测试结果就蛮不好的,刚入学的时候,中国学生比俄罗斯、印度的学生数学、物理都好,越到后来领先的程度越少差别越来越小,有一部分俄罗斯学生还反超中国学生特别是批判性思维,对一个意见提得出不同意见,提得出质疑的意见,这种能力比较欠缺。所以要真正做出好的工作,很需要培养质疑的能力,听到一个意见以后不要马上接受它,要去想想和你过去学到的东西、和你相信的东西是不是一致的。
供稿:吴立德
整理:郭福英
编辑:韩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