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充分体现我校老教授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进一步推进老同志在当前“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背景下发挥作用,2019年,我校设立了老教授课程思政工作坊。在老干部党委的统筹下,由老干部工作处牵头负责,联合退休教职工工作处、教务处、党委教师工作部等部门,共同推进老同志参与学校中心工作。2020年,工作坊联合《复旦》校刊,开设“老教授谈教书育人”专栏,特邀各院系老教授结合多年来教书育人的经验,围绕“我所开设过的课程”、“我当年是怎么编写教材的”、“我当年是怎样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的”、“我们当年是这样备课的”等主题撰写文稿,传授经验为主,讲述当年故事为辅,为广大在职教师备课、教学、教材编写等方面提供借鉴和参考。
百廿复旦正青春,教书育人薪火传。“老教授谈教书育人”专栏系列文稿,既在《复旦》校刊定期发表,也在《校史通讯》和复旦主页“相辉笔会”刊登,并陆续在“旦园枫红”公众号加以推送,通过个人回忆与历史见证,展现120年来的复旦故事、师德传承和教书育人的温度。
探索科普写作之路

顾凡及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退休教授,计算神经科学专业。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先后在中科大生物物理系、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任教。退休后主要从事科普著译,已出版八本科普著译,曾获七次奖项。获得第四届认知神经动力学国际会议(瑞典)授予的成就奖,以及2017年上海市科普教育创新奖(个人贡献二等奖)。
不觉已到了耄耋之年,回顾一生,可以说自始至终都和科学结缘,遗憾的是没有对社会做出多少贡献。科普是我在一生的一头一尾两段时间里,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我自身而言,2004年退休后这十几年里从事科普写作可以算是我自以为做得比较好的年头,其原因无他,是因为有充分的时间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写作和翻译与脑科学有关的科普作品,乐在其中。一旦做事成了享受,就不再是要我做,而是我要做了。我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与同好切磋,共同讨论如何做好科普写作,为提高国民的科学素质共同略尽绵薄之力。
科普书触发了我青少年时代对科学的憧憬
我在中学时代课余最大的爱好就是阅读科普读物,特别是前苏联科普作家别莱利曼写的一套趣味科学丛书令我爱不释手,这些书融科学与人文为一体,用讲故事的形式阐明科学的道理,常常有使我脑洞大开的感觉,书中经常引用凡尔纳科幻小说等文学作品中的内容,使人读来兴趣盎然,而又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虽然读了至今已近一个甲子,但是记忆犹新。例如我至今还记得在他的《趣味几何学》一书中就介绍了如何根据相似三角形的原理,只要用一把大一点的三角尺就可以间接测量高耸入云的树的高度。很巧的是,不久之前我读到学长李大潜院士在谈他如何走上数学研究之路时也提到了同一个故事。由此可以印证像别莱利曼这样既有趣又有“干货”的科普作品对年轻人影响之深。正是这样的科普作品触发了我青少年时代对科学的憧憬。
2004年年初退休以后,开始考虑退休生活怎么过的问题。由于长期从事和计算神经科学有关的科研和教学,对脑和心智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退休之后,没有了实验室,没有了学生,也没有了科研经费,再要从事科学研究显然是不现实的。但是由于以往学习和工作的积累,和国内外的脑科学家依然保有联系,有问题依然可以向他们请教和讨论,仍然可以利用学校的图书馆资源,当然更可以利用网上资源,从事脑和心智问题的科普写作和翻译工作依旧实际可行,并且有了充裕的时间,在这一点上较之在职人员甚至有一定的优势,因此就萌生了以脑和心智的科普作为余生“事业”的想法。而触发这一点的是一次和郭爱克院士一起去日本参加学术会议,在路上聊起一位我们两人都认识的德国科学家,我们能想起他的工作,他的脸型,以前一起参加学术会议时有关他的故事,但是无论如何就是想不起他的名字。我们两人苦苦想了很久,甚至想到过和他名字有一个音节相同的另一位德国科学家的名字,但就是想不起他的名字。后来我准备放弃了,说反正第二天我们在会上会遇到另一位德国朋友,我们去问他吧。爱克不同意,说这太扫兴了,我只好再想,而就在一瞬间,他的名字突然跳了出来,我脱口而出。爱克也很高兴说:“对,记忆真是件神奇的事。”我就说:“大脑真好玩。”爱克讲:“那你何不就用《好玩的大脑》作为书名写本科普书呢?”巧的是,事后不久杨雄里院士打电话来说少年儿童出版社要他推荐个人写本有关脑科学的科普书,问我愿不愿意写。这样就有了我退休后的第一本科普作品《好玩的大脑》,此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开始了我作为科普作家的晚年生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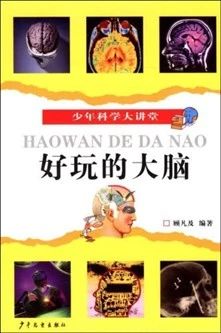
顾凡及编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年版
努力写出熔科学性、趣味性和前沿性于一体的脑科学故事
不过真要认真地做好脑科学科普对我说来也并不简单。虽然我从大学毕业以后就开始从事计算神经科学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但是由于自己并非神经科学科班出身,在大学里念的甚至都不是生命科学,工作后主要是要用到什么学什么,并没有系统学过神经科学的课程。自己熟悉的内容范围过于狭窄,不能胜任脑科学科普的需要,因此不得不重新学习。开始时自己也有过顾虑,以像我这样背景的人来写脑科学科普是否合适,不过后来我想硕博连读也就是读四五年,我现在即使是从头学起也并不算晚,这样我就重新拿起一本深入浅出、图文并茂的优秀神经科学教材,像学生一样认真阅读。我当时的想法是,希望自己能像别莱利曼一样写出一本《趣味脑科学》!不过和别莱利曼略有不同的一点是,他所介绍的物理学、力学、几何学、代数学等都相对比较成熟,而脑科学则是近年来才迅速发展起来的,所以与时俱进,介绍科学界最新的认识就更显重要。因此我就把熔科学性、趣味性和前沿性于一炉作为自己的写作目标(当然应用性也是科普要考虑的重要内容,如果也能做到,当然最好。但是对基础科学的科普来说,则在某些时候可能做不到这一点,这和应用科学和技术的科普有些不同,而更为主要的是我不擅长于此)。

顾凡及教授
科学性是科普读物的灵魂,虽然不能要求科普作品中所讲的内容一点错都没有(事实上,一些前沿的开放问题,科学界本身就还没有共识,其中的某些观点可能在将来被证伪),但是科普读物的内容应该都有根据,而不是道听途说,也不是猎奇,更不能容忍伪科学。科普读物不只是介绍知识,更重要的是介绍获得这些知识所应用的方法,不仅应该让读者知其然,更重要的是要让读者知其所以然。
我相信趣味是最好的教师,一本书如果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那么读者就会“我要读”,而不是“要我读”。科普书应该能激起读者的好奇心,使读者热爱科学,让读者从阅读中找到乐趣。科普书不是教科书,也不是应试参考书,更不是和自己工作有关的专著,如果没有趣味,一般读者为什么要读?这就要求科普作品不仅要行文流畅,而且尽量通过讲故事的形式来讲道理,具体、生动,寓教于乐。这要求科普作者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尽量向文理融合努力。
在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知识在飞速更新,所以一本好的科普书应该与时俱进,跟上科学的发展,向读者介绍当前的科学认识和新发展,而不是已经过时了的陈词滥调。这就迫使我不得不努力学习,不仅要读新的教科书,还要搜集当前国内外和脑科学有关的高级科普书、科学网站,以至有趣的专著。注意像Nature这样比较权威的网站上有关的书评,及时找有重要影响的新书阅读和思考。这十几年来,我给自己定了个雷打不动的规矩:每周至少有两天定时浏览国内外有关脑科学的主要网站,以使自己能跟上脑科学发展的步伐,及时知道当前热点和重大事件,为素材积累和跟踪发展趋势打下基础。
一本好的科普书还应该图文并茂,有时一张好的插图所说明的问题比一页文字叙述更有效,有趣的插图更增加了趣味性。在我刚开始写作时,关于插图的知识版权问题还不那么严格,我可以从书、刊、网站上引用。但是现在插图问题已经成为我写作的主要问题之一,遗憾的是自己并非美术家,没有能力自己画。引用他人的图画牵涉到版权问题,需要和出版社密切合作,或者提供草图和设想,请人画,或者找没有版权问题的图。我常常不无遗憾地想,如果我能像寿天德、林凤生教授等会自己绘图该有多好!以上可以说是我始终坚持的科普理念。我想也是所有优秀的科普作品都可能要有的元素。
在我开始科普写作时,我的定位是向公众,特别是年轻一代讲有关脑和心智的有趣故事。此类书的主要目的是引起读者对脑和心智强烈的兴趣和好奇,向读者介绍这方面的有关知识和最新进展。内容不求其全,每个故事都可以独立成篇。每一篇都从神经科学家曲折的发现故事或者一件令人不解的奇事或者当前的某个热点说起,最后从中说明一个科学道理。这就像在浩瀚的脑海边上拾取一个个美丽的贝壳,汇集起来按类排列展示,让观众在赏心悦目的同时,产生对大自然的热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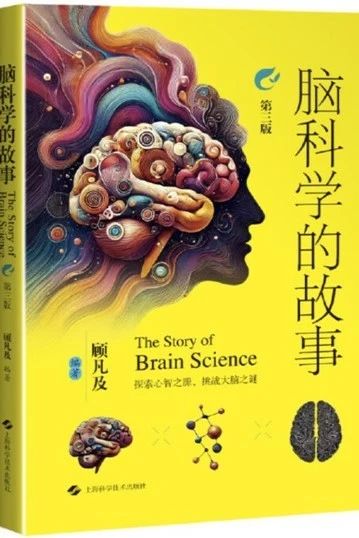

讲清楚脑科学知识的来龙去脉,知其所以然
在写完《脑科学的故事》之后,回忆自己读过的神经科学教科书,里面有那么多的知识,就向自己提了些问题:这些知识是怎么得来的,怎么知道这些知识是对的?还可能有其他解释吗?对这些问题我很好奇,我想这也许是许多读者也会问的问题,何不就这个主题学点东西,再写一本科普书呢?于是自己就去找了些神经科学史的书来读,当感到其中一些重要发现讲得不够详细和生动的时候,就再找相关的科学家传记或回忆录来读。美国神经科学学会主编的神经科学家自传系列和诺贝尔奖委员会要求得主撰写的自传都提供了第一手、生动及时的材料,这些材料在这方面非常有帮助。
由于神经科学史不可能谈及当代的最新进展,所以还得读最新进展的有关报道,诺奖得主的演讲。此外考虑到读者不一定熟悉有关背景知识,需要把这些材料也综合进去一起回答上面的问题,这样写成一本书也许是个好主意。我的这些想法得到了陈宜张院士的支持和指导。这时我又恰恰读到2000年诺贝尔奖得主坎德尔的一段话,更坚定了自己的决心。他说道:“在想深入研究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通过了解以前的科学家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从而逐渐得出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不但想知道哪些思想路线最后取得了成功,而且也想知道哪些思想路线最后失败了,并且是为什么失败的。”这一切不正像是一部谜团重重的悬疑小说吗?你还能想出有比揭开脑和心智之谜更难的谜题吗?另外,这部小说到结尾还没有真相大白,还有许许多多疑问有待澄清,有许多地方有好几种可能的不同解释。即使是柯南道尔和克里斯蒂也想不出这样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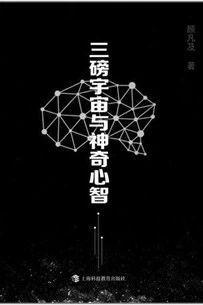
左图《脑海探险:人类怎样认识自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4年版
右图《三磅宇宙与神奇心智》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
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写出了《脑海探险——人类怎样认识自己》和《三磅宇宙与神奇心智》这两本书。诺奖得主冯·贝凯希说过:“事实并不十分重要,教师真正应该做的只不过是指出某些方向。我们可以由此开动自己的大脑。所以老师教不了我们太多东西。他真正应该教给我们的是对工作的热爱,并引导我们对某些领域始终保持兴趣。我总是以这种方式来看待我的老师,我并不想向他们学习事实,只是想找出他们工作的方法。要是一位教师(特别是大学教师)不能教给学生研究方法,那么他就给不了学生什么有用的思想,这是因为,学生将来在工作中要用到的事实一般来说总和他在课堂上所讲的事实有所不同。但是,真正重要并对一生都有用的是工作方法。这就是为什么我只对方法感兴趣。”我想不但教师,科普作家也应该这样,不仅介绍知识,还要介绍思想方法,不单是抽象地介绍原则,而是通过具体故事介绍,使读者有所感悟。
开放问题,合理质疑,引导读者同步思考前沿难题
在上述思考的过程中,我又给自己提出新的问题:书上讲的现在有关脑和心智的认识都一定正确吗?即使是上了教科书的被认为是“定论”的问题是否真的那么确凿无疑?当然如果不仔细审视得出那些“定论”的研究过程,就没有理由无端怀疑。正是在我第二步的过程中,在力图搞清楚现在的认识是怎么来的过程中,会发现有些立论根据不足。把自己放在一个学生甚至是孩子的地位去读、去想是有好处的,也许倒可以在某些情况下看清“皇帝的新衣”。我自己在以前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时有一个感慨,就是在报告人报告后,许多人能立即对报告内容提出问题甚至质疑,然而我却很少能提问题,而这也正是一些国外教授认为不少中国学生的不足之处。这除了语言障碍之外,科学文化的不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李政道说过:“要开创新路子,最关键的是你会不会自己提出问题。能正确提出问题,就是创新的第一步。”提出疑问和讨论一些难于下结论的开放问题也是当下前沿科学科普化的一个命题。时下科普文章中一般最多也只是在文章的最后比较简单地提一下本领域前沿的一些进展,但是要此为主题写成一本具有可读性的科普作品则少有先例。当然现在在国外也开始出现一些有关脑科学“迷思”的书可以说是属于这类书,可惜这样的书还不多。

2022年上海市科普教育创新奖颁奖典礼
对我说来碰巧的是,2012年当欧盟人脑计划将启未启之时,由于我本人对脑科学和信息科学的交叉领域一直怀有强烈的兴趣,所以对该计划的前身——2005年启动的蓝脑计划早就一直在跟踪关注,从其业绩中我对新计划所提的目标——十年内造出人工全人脑深表怀疑。我曾经和一位同事讨论过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这些人都是聪明人,他们不会想不到连我们也能想到的问题。”这似乎是一条强有力的理由,但是这并不能令我信服,因为我知道皇帝的大臣们也是些聪明人,但是利害关系使他们假装“看到了”皇帝的新衣。于是我开始和国内外的一些同行讨论这个问题,巧的是一位对脑科学有强烈兴趣的德国IT工程师卡尔·施拉根霍夫博士,也和我一样对这些问题怀有强烈的兴趣,而且也已退休。因此虽然我们两人从来没有见过面,而是通过我们两人的一位共同朋友的介绍而开始网上通信。先是关于对欧盟人脑计划的评价,以后进而讨论脑科学和人工智能的种种开放问题。难得的是,他不仅每问必答,而且为了我的问题,甚至专门订购我讲到的某本书,在读了之后再和我讨论。在这样讨论了三年之后,他把我们的来往通信邮件重新发给我(因为我把早先的邮件都已删去了),建议在此基础上写成一本书。重读旧信,觉得还有点意思,卡尔建议的书信形式也比较适合这样未有定论的讨论和争论的主题。这样就有了我们三本一套的书系——《脑与人工智能:一位德国工程师与一位中国科学家之间的对话》,就脑科学中的一些开放问题、人工智能的进展与前景、意识问题、脑科学大计划以至科学方法论问题进行讨论和争论。当然我们并不奢望我们的看法都是对的,事实上甚至我们两人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也有分歧,有些问题我们也拿不准应该如何认识。我们只是力图以理性思维来思考这些问题,并引起读者的思考,让今后的实践来检验孰是孰非。希望读者也能对脑科学和人工智能上的问题进行独立思考,自己进行判断,而不是人云亦云,盲目跟风。我想好的科普最后必定要走到这一步,而不只是普及知识。
领悟大师们的治学之道,学会以理性思维独立思考,善于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
在读科学家的传记和回忆录时,我深为脑科学家的治学之道所折服,深恨所知太晚。我想如果我能早点学习大师们的治学之道,那么至少会比我以前所做要好得多,当然往者不可追,但是我想如果我把这些写到科普作品里去,至少可以让后来者不会重蹈我的覆辙,从而对社会有所贡献。
和一般的传记文章有区别的地方是,我感兴趣和叙述的只是传主的成才之路和他们在作出自己主要贡献时的奋斗故事,他们的感悟金句,以及他们的治学之道,而非其他。这样就写了不少科普文章,并在此基础上最后汇集成一本书——《发现大脑》。这本书的目的是通过故事向读者具体介绍大师们的成才之路和治学之道。正如冯贝凯希所言,重要的不仅是介绍大师们的发现,更重要的是要让读者体会他们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2020年顾凡及教授参加科普作品研讨会
在开始写的时候,我是准备写出我读过的杰出脑科学家共同的成才之路和治学之道。但是后来发现这些大师的成才之路可谓五花八门。尽管其中不乏神童或学霸,但是也有令父母头疼不已的问题少年、街头儿童、邻家少女和文艺青年;他们中虽然不乏医学世家,但是也有平头百姓、贫困的移民家庭甚至身世不明者。因此并没有什么标准的成才之路模式,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只能放在他们所处的具体环境中才能理解他们怎么样脱颖而出。尽管如此,就治学之道来说,他们确实具有许多共性。这突然使我想起从小学、中学、大学求学以至工作到退休的母校的共同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可惜的是我以前一直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直到在仔细思考这些大师们的治学之道时,我才突然感悟到如果与时俱进地解释这条校训,那么它就是关于志、博、思、问四个方面。“志”就是对科学的无限热爱和无穷的好奇心以及百折不挠的毅力;“博”就是不但有专长,还要跨学科对相关领域有相当深入的认识;“思”就是要理性地思考,不盲从;而“问”则是要善于提出问题,并经常和同事以至学生讨论问题。我这样说过于简单,也肯定不够全面。真要想理解他们的治学之道,也不是讲几句抽象的原则就可以领会的,而要放在他们具体的环境中,通过他们奋斗的故事才能有所感悟。我希望我的这本新作对正准备走上科学道路的年轻一代会有一点启发。
虽然是从事后回顾,我走过的科普写作之路似乎还是符合逻辑的。但这并不是我有什么先见之明,事先有计划的安排。而只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好学的学生的位置上从头学习必然会产生的问题。总之,我认为科学性、趣味性和前沿性是任何一本好的科普作品都应该有的元素,应该努力做到文理融合、寓教于乐。另外,介绍现有知识的来龙去脉、引导读者思考其中的开放问题也很重要,介绍大师们的治学之道和研究问题的方法更是科普的极为重要的内容,还有我未能做到的应用性也非常重要,把所有这些因素或其中某些因素融合到科普作品中去,应该是我今后的努力方向。

顾凡及教授
以上所讲只是自己在这十几年来从事科普写作方面的一些追求,囿于自己的水平,虽然把理念定得比较高,但是未必都能做到,不过“法乎其上,得乎其中。”把要求提高一点,也许能迫使自己把事情尽量做好一点。
回顾自己的科普写作之路,也有许多遗憾。我的科普著作,除了和卡尔合作的一套书系之外,其实都属于编著性质,只是搜集了许多他人的工作,在经过学习、消化吸收之后,把材料重新加以组织,而极少真正属于自己的原创。特别是因为自己在科研生涯上没有做出什么像样的工作,因此不可能写出像达尔文、法拉第、克里克、拉马钱德兰、萨克斯这样科学大师基于自己工作之上,既富文采又有自己创意的科普作品。我国科普界的前辈卞毓麟先生把这称之为“元科普”,我也深以为然。随着我国国力的上升,正涌现出越来越多的重要科学成就,我热望有越来越多在一线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把他们自己的故事写出来!这样的作品才是真正的元科普,而可以影响久远!
供稿:顾凡及
协助整理:郭福英
编辑:韩 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