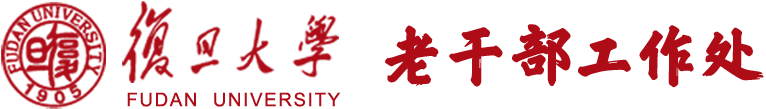为充分体现我校老教授的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威望优势,进一步推进老同志在当前“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背景下发挥作用,2019年,我校设立了老教授课程思政工作坊。在老干部党委的统筹下,由老干部工作处牵头负责,联合退休教职工工作处、教务处、党委教师工作部等部门,共同推进老同志参与学校中心工作。2020年,工作坊联合《复旦》校刊,开设“老教授谈教书育人”专栏,特邀各院系老教授结合多年来教书育人的经验,围绕“我所开设过的课程”、“我当年是怎么编写教材的”、“我当年是怎样在教学中对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的”、“我们当年是这样备课的”等主题撰写文稿,传授经验为主,讲述当年故事为辅,为广大在职教师备课、教学、教材编写等方面提供借鉴和参考。
“老教授谈教书育人”专栏系列文稿,既有在《复旦》校刊定期发表,也有在《校史通讯》和复旦主页“相辉笔会”刊登。我们将在本公众号中陆续加以推送。本期与您分享李大潜教授的教研心得,并借此对李教授表示敬意和谢意。
我的几位大学基础课老师

李大潜
195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1966年该校在职研究生毕业。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7年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2005年当选为法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复旦大学教授。中法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曾任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中国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理事长,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联合会执行委员。对一般形式的二自变数拟线性双曲型方程组的自由边界问题和间断解的深入研究,对非线性波动方程经典解的整体存在性及生命跨度的完整结果,对一维拟线性双曲系统的精确能控性及能观性的系统成果,以及近年来对双曲系统的精确边界同步性及逼近边界同步性的开拓研究,均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得到国际上的高度评价。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对各种电阻率测井建立了统一的数学模型和方法,据此制作的微球形聚焦测井仪器成功地在国内多个油田推广使用。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015年获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联合会(ICIAM)苏步青奖。
2023年4月18日在复旦大学成立“上海市教育系统关工委李大潜导师工作室”。
大学一年级的数学课,对我们这些中学里数学学得好、也自以为学到手的学生,确实打开了新的天地,使我们对大学的数学,不由得充满好奇与心存敬畏。当时有三门数学课程: 解析几何、高等代数和数学分析。

周慕溪先生
解析几何课程是周慕溪(周绍濂)教授开的。他是早年法国巴黎大学的博士,人长得高高瘦瘦的,只带几张卡片就来上课,真有一点教授的派头。解析几何用代数的方法解决几何的问题,因为在中学已学过平面解析几何,现在进入到空间解析几何,倒不觉得有太大的困难。周慕溪先生在课上有时还给我们介绍一些经典的数学难题,记得有一次讲了四色问题 (用四种颜色就可以做任意的地图),说这个问题很难,现在还未解决,但说如果改为五色问题就很容易证明了,并画图做了说明。他说的这些,我当时虽不知所云,但还是觉得很有趣,感受到数学的魅力及威力,也激起了自己探索未知的朦胧愿望。周慕溪先生是点集拓扑与微分几何的大家,后来还给我们上过微分几何的课,也是手执几张小卡片来讲课的。最近才知道,他1945 年就在正中书局出版了《人寿保险计算学》这一著作。改革开放后,我们大力提倡保险精算的研究方向,复旦还在1994年成立了《友邦-复旦精算中心》,至今仍是我校应用数学方面的一个亮点。追根溯源,周慕溪先生看来是中国保险精算的第一人。然而当时,保险精算应该算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学问,是不能加以提倡的,我们也根本不知道这些。


2023年4月18日上海市教育系统关工委在复旦大学成立“李大潜导师工作室”,图为李大潜院士在揭牌仪式上发言

金福临先生
数学分析(即微积分)课程要连续讲三个学期,是一门重点的课程。在这门课程中,要在中学学过的初等数学的基础上,实现由有限到无限、由静止到运动和由直到曲这样一些观念性的转变,进入高等教学的范畴。中学数学学得再好,这一个弯子也是不容易转过来的。给我们讲这门课程的是金福临先生,他当时才三十岁左右,比我们大不了多少,职称也只是讲师,但大家对他都很尊敬。他当时用的是苏联斯米尔诺夫编的“高等数学教程”第一卷,由孙念增翻译成中文出版的。金福临先生对教材钻研得很深,讲得极有条理。他讲得快,写得快,也擦得快。将他在黑板上所写的完整地记录下来,就是一个很好的笔记,课后就可以用来复习了。由于他认真系统的讲授,我学起这门课来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困难,从初等数学到高等数学入门的这一关就这样轻轻松松的过来了,而且在微积分的理论和计算方面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到现在都发挥着作用,因而一直十分感激他。当时同学间还传说,他在 600 号三楼的办公室晚上总是灯火通明,他的那种广泛涉猎、好学不倦的精神和作风,对我也起了很大的表率和示范作用。一位刚刚从浙大调到复旦、且升上讲师不久的老师,由于苏步青及陈建功两位老师的熏陶及长期形成学术传统的感化,竟能这样模范地发挥一个教师的作用,印证了苏步青先生所说的那句话“要将自己的学校看成最好的学校,要将自己的老师看成最好的老师”,实在是金玉良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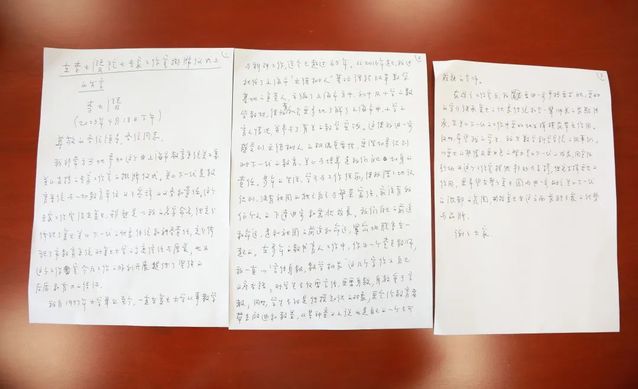
图为李大潜院士在工作室揭牌仪式上的手写发言稿

陈建功先生
到了大学三年级,要学“实变函数”这门课。讲课的老师是我们仰慕已久的著名数学家陈建功教授,他是这一领域的权威,大家都非常庆幸和高兴。然而学了不久就发现,实变函数实在是一门很难的功课,而陈先生讲课用的是绍兴官话,讲得又十分简洁和精炼,很少做一些铺垫和说明,有时当他宣布定理证毕的时候,我们还都似乎觉得才刚刚开始,一点也摸不着头绪。他用作教材的自编讲义《实函数论》(这是当时唯一一本不是苏联教材的讲义!),也同样十分简洁精炼,无异于一本天书,而且当时没有正式出版,是刻写油印的,还有不少印刷错误。我自己在课上听得不太明白,甚至有时是不明不白,课外要花两三倍的时间复习,逐字逐句地破译这本天书似的讲义,补充一些过程及细节,改正一些印刷错误,也写下一些自己的点滴体会,一步步地消化理解有关的内容。当时认为这样做太花时间,也颇以为苦。但破译了这本“天书”,不仅检验和培养了自己的毅力和能力,也使自己增添了信心和勇气,以后碰到再难的“天书”都不在话下了。现在看来,当时这样做,最多也只是达到了杨武之先生所说的“局部精通”的程度,远远还谈不上“融会贯通”,但已使我终身受益。反复思考,深入理解,对于学习数学这门科学的重要性,由此也可见端倪。
陈建功先生课上还讲过一句话:“最简单的证明就是最好的证明”,同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题可以多解,一个定理可以有好几种不同的证明,到底哪一个是最好的呢? 这就要有一个判断的标准。毫无疑问,最简单明了的证明,最能直面问题的本质,痛快淋漓地使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比起那些故弄玄虚、颠三倒四、走了不少弯路的证明,要高明了不知多少倍。对数学的认知和欣赏,是要有一个美学标准的。陈先生的这句话,作为一个美学标准,一直是我努力追求的一个目标。所有这些,最终使我认识到: 数学学习的好坏,不能单纯地追求解题的数量和速度(现在的说法就是“刷题”),而是要看是否理解深入、运作熟练及表达清晰这三个方面,这里所说的运作泛指运算及推理等环节,而三者的关键是要深入的理解。认识到这一点,并努力加以实践,才能真正跨入数学的大门。
欢迎继续关注
“老教授谈教书育人”系列推送
来源:上海市教育系统关工委李大潜导师工作室
供稿:李大潜
摄影:成 钊
编辑:韩 佳